2012-11-26 08:24:00 來源:大河網-河南日報
網友評論0條 查看全文(共1頁)

暢談《一九四二》,劉震云神采飛揚。
。
劉震云,1958年生,河南延津人,著名作家,電影《一九四二》的編劇,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此前有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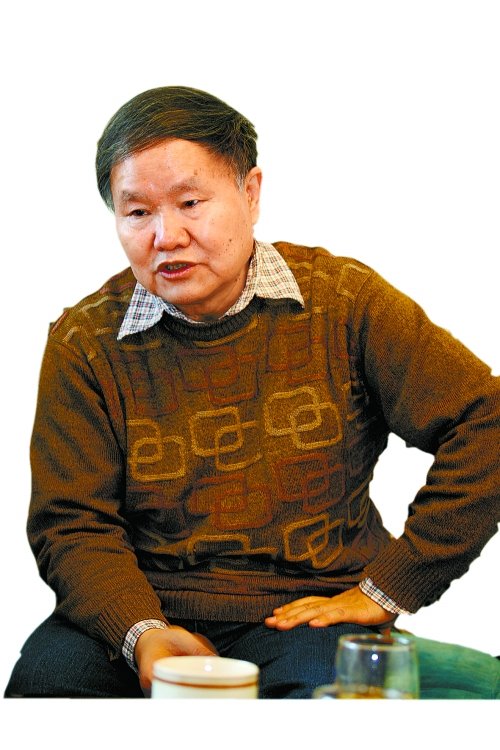
劉慶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著名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煤炭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其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國文字,其中小說《神木》拍成電影《盲井》。

“好電影是由好作者決定的,《溫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說,震云又創造了非常好的劇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
1942年,河南遭遇“水旱黃湯”,導致300萬人被餓死、300萬人流離失所。然而,幾十年后,即使是當年親歷者也對此喪失了記憶。為此,河南作家劉震云寫成調查體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發表在1993年的《作家》雜志上,隨后由劉震云編劇、馮小剛拍成電影《一九四二》,并將于11月29日公開上映。本報記者赴京對此進行專題采訪,為您解密有關“1942”從小說到電影19年艱辛成長的背后故事。
劉震云托河南日報給家鄉父老帶話:
河南讓我知道了大小多少東西南北
11月24日下午5點,河南日報一行記者如約來到威斯汀酒店采訪劉震云,我們轉達了朱夏炎社長的問候,并邀請劉震云方便的時候到我們河南日報做客,劉震云爽快地說,一定去,年底之前就成行。
我們拉了會兒家常后,劉震云跟記者談起了“1942”。
記者:您寫作《溫故一九四二》的初衷是什么?
劉震云:與“1942”相遇非常偶然,它根本不在我的寫作規劃,作者和作品都有生命,二者相遇具有偶然性。1990年,我看到錢剛寫的《唐山大地震》,才知道1942年河南餓死了300萬人,個體死了,是生命,會有感覺。而300萬只是數字,與二戰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了100萬比較,才感到很震撼。
后來在采訪1942年的那些親歷者時,發現他們都忘了。遺忘比沖擊力更大,我再次受到震撼。之所以忘,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不重要,再一個是,重要,但太頻繁了,災難像家常便飯。
記者:那么為何后來又考慮著把它拍成了電影?
劉震云:當1993年,小剛(馮小剛導演)提出要把《溫故一九四二》改編成電影時,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調查體小說,就是材料的堆積。是電影元素之外的東西吸引了小剛,他喜歡它的味道、態度、幽默感成分。嚴肅的態度面對災難已經有了,比如《辛德勒名單》。冷幽默對付生死特別獨特,體現出民族面臨災難頻繁時的態度。態度比故事、情節、細節更重要,這是小剛拍攝最為關鍵的因素。
記者: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劉震云:當時復雜的政治、社會及國際環境等比300萬人更重要。1942年災難出現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之外,跟戰爭、政治、積貧積弱都有關系。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入中國,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國才正式對日宣戰。就好像一群流氓闖到家里,打一巴掌躲一下。當時的國民政府準備把河南作為負擔拋給日本,日本對此也不提供救濟。這是一個大和小的哲學問題,放棄河南是“小”,亡國是“大”。
面對死亡,歐美人會問誰讓我死的?河南人的態度是什么?中國式幽默!這也引起我的思考:電影之外的態度。
雙方討論,我們決定在逃荒路上找。我們重走了當年逃荒的路、白修德(當年調查報道河南災情的美國記者)的路、日本進攻的路。
什么樣的態度是最好的態度?那就是沒態度!你的態度就是災民的態度,災民的態度就是你的態度。
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角落,人生都有被遺忘的角落,而遺忘的角落,則隱藏著歷史,散發著人性微弱的光芒,蘊含著真實的歷史、過去和明天。
記者:《一九四二》想告訴人們什么?想傳達一種什么樣的意義?
劉震云:這個電影投資了2.1億元。觀眾要看的是一個好電影,無論是喜劇或者史詩性作品,都不要低估觀眾的智慧,觀眾觀影習慣超過作者的期待。
小剛對《一九四二》有信心。試映時,有各個類型的觀眾,但看后都會有一個變化,變得善良了、感動了、被震撼了。
記者:小說和電影有著不同的運作模式、邏輯和訴求,您似乎跟電影很密切,當二者發生沖突時,您是如何平衡的?
劉震云:我沒有平衡。第一,我跟電影不密切,只是跟幾個導演朋友密切;第二,我只懂小說,我是一個好作者,但不是一個好編劇,之前合作也會有爭論,但沒有一個導演堅持19年拍這個電影。
我的小說都不適合改成電影,小說和電影完全不同,小說像大海,下面暗流涌動;電影像奔跑的河流,像瀑布,方向和目的不同。電影《一九四二》達到了一種新的高度:真實,創作者沒有態度,表演到無我狀態。
記者:據了解,作為當年災難發生地,電影外景卻沒有一處選在河南,多是在山西省選的外景。家鄉延津的人民很期待,說您小說里好多事、好多人都是老家村里的事、村里的人,“震云為啥不在老家拍呢”?
劉震云:沒有在河南選外景,是因為我們重走災民路,發現河南的發展日新月異,找到1942年的房子確實很難。將來拍《一句頂一萬句》了,就在老家拍。
記者:您的小說和電影都是對人性的探討,魯迅是對國民性的批判,您卻是對人性的包容,為什么?
劉震云:批判里面也有包容,批評性就是建設性,因為歷史的真實在里面。批評就是不能干什么,這就是建設性。19年間,隨著年齡的增大,我也慢慢地變得比較平和,人人都是哲學家,我收獲的更多的東西,就是無我的創作態度。
記者:前一段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很多評論認為,您也是諾獎的有力競爭者,您怎么看?
劉震云:莫言是我的兄長。我不知道,莫言獲獎,為啥都跑來問我的感受。就像哥哥娶了嫂子,他的洞房花燭夜,卻問我有啥感受,我只能說祝他幸福。其實,獲不獲獎是外在的東西。莫言應該獲獎,對中國文學而言,應該娶個嫂子。
記者:有媒體就小說里面“日本進攻中國,老百姓繳了國軍的槍”等細節,再次提出河南人形象問題,您怎么看?
劉震云:跟很多文明一樣,河南依河而居,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問問母親來自哪里,母親從這里來,因此具有包容性。
不覺間,原定40分鐘的采訪時間過去了。工作人員不斷催促結束采訪,劉震云都會笑著向她解釋:“沒關系,沒關系,這是家鄉的媒體!”后來,由于其他約定媒體到場,我們不得不結束采訪。劉震云笑著大聲說:“我最后再專門給家鄉媒體說幾句話。”他滿懷深情地說,河南對我的影響至關重要,我的作品有2/3與河南有直接關系,包括地名、人名,電影《一九四二》的開頭就打上了河南延津;家鄉給了我世界觀和方法論,比如“東西南北、大小多少”;河南人非常幽默,有羊肉就會做成羊肉燴面,而陜西卻做成了羊肉泡饃;河南人很包容,比如燉菜、比如“喝酒先敬你三杯我再喝”!
【記者印象】劉震云非常健談,也非常善談。劉震云很詼諧幽默,也很睿智深刻。劉震云對家鄉的感情很深,這尤為讓人感動!
名動京華的“北京三劉”河南占其二
細聽劉慶邦談“劉震云與1942”
11月24日上午,河南日報一行記者如約來到原煤炭部家屬院劉慶邦的家里,我們轉達了總編輯趙鐵軍的問候。見到家鄉人,劉慶邦顯得很激動,拿出1993年《作家》雜志刊發北京“三劉”(劉恒、劉震云、劉慶邦)的作品小輯,在那里首發了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劉慶邦的話題就從這里開始。
“1942”,為民族保留了記憶
震云的這部小說似乎不太像小說,像資料調查一樣,即使算是文本調查,也不是很深入,對當時的情況說得很少。
當時聽說要把它拍成電影,我覺得電影難拍,因為它沒有故事、沒有貫串性的人物。但重大事件值得記錄、值得拍攝,這不光對河南有意義,對整個歷史也很有意義。人喪失了記憶,就像一個傻子;一個民族如果淡忘歷史、喪失記憶,那就更可怕,尤其是對重要記憶的喪失。
作家有責任為民族保留記憶,震云寫《溫故一九四二》就是為民族保留了記憶,現在又拍成電影,通過藝術記錄“1942”,傳播更廣泛,讓全國甚至全世界重新記起沉痛歷史。
肚子餓了,是最大的問題
你問很多老人1942年的事,他們大都說不知道,但你要說民國31年,他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我沒有經歷1942年的災難,但母親給我講過,我印象很深刻。
我母親是開封尉氏人,1942年那里也是重災區。母親說當時鬧蝗災,吃飯碗里都能落螞蚱(蝗蟲),用麻袋隨便一弄就是一麻袋。我祖父就差點餓死,全身浮腫、奄奄一息。當時財主也趁機買地,我家就一畝半地,財主給了一斗高粱,就把地買了去。
1942年大旱,糧食沒收獲,尤其是冬天餓死的人特別多。傳說街上有賒飯吃的,救濟喝粥飯。冒著大雪,很多人就往街上去,餓得走不動,就在雪地里爬,有的爬不到地方就死了;那些最后爬到街上的,卻發現根本沒賒飯吃這回事,就更絕望了。
我也吃過柿樹皮,用火烤,烤黃咬著吃,柿子不熟是澀的,柿樹皮也很澀。其實,任何時候,對人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
1942年苛捐雜稅重,當時又沒啥工業,靠老百姓交糧支撐軍隊。當時國民黨當權者如果能體恤民情的話、不磨蝕生命的話、有人文精神的話,不至于在自然災難之上雪上加霜,使人民得不到救濟。
保留記憶,通過批判、回顧和揭示,讓人們記得沉痛的苦難,以避免重蹈覆轍。
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不同,震云在《溫故一九四二》中所揭示的是在饑荒狀況下的一個人性狀態,生存最本能的部分是要活命。在這種狀態下,一是弱肉強食,二是家族的根要傳下去,所以賣閨女、留兒子,被逼到絕路了。
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根,魯迅的根在紹興、沈從文的根在湘西等,一個作家只有牢牢地扎“根”,才有記憶,尤其是少年的經歷對作家尤其深刻,少年時的記憶是一張白紙,印象就深刻得很。
這種記憶是改變不了的夢境,我一做夢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人可以到處走,去煤礦、去城市,環境會有很多改變,夢卻改變不了。為什么少年時代的夢都是老房子?少年的記憶特別頑強,一寫作就會想到故鄉的人和故事,想到故鄉的自然環境,這可以說是作家的創作規律,每個作家都是這樣。
當然作家也四處采風,但看到的都是別人的東西。而回老家則會激活記憶,創作源泉也就源源不斷。
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34年。北京是文化中心,站位比較高,上來就是和全國對話、和世界對話,對開闊作家胸襟、境界有幫助。
相對來講,故鄉文化則是對農業文明的回望。城市文化相對封閉,農村文化中的人心、人性則是開放的。比如在農村,有個啥故事,全村人、甚至四鄰八村都會很快知道。在城市,人與人之間則比較隔膜、封閉、戴著面具,即使對門,也互不認識。
農村類的東西,自然風景、民俗風情體現了很多東西,寄托著一種鄉愁、一種鄉思。
喚醒人的記憶
對作家來講,對閱讀文本,只有更多人看到才能夠體現出它的價值。我也希望將自己的小說拍成電影、電視,因為它們是強勢媒體。我的小說《神木》拍成電影《盲井》,就使得作品被國際上所認識。
但寫小說不能想著為了拍電影,好多作家就因此“回不來了”。小說創作和電影創作不是一個路數,小說是心靈化的東西,電影則會多少影響文學品質。我還是要好好寫小說,能改(成劇本)就改,不能改就不改,人命不強求,強求不行。
電影《一九四二》會有很大影響,但對1942年的災難,有小說、有電影等“軟”的紀念就夠了,不一定非要用硬件的東西,類似的災難太多,不太可能都建博物館。小說和電影能喚醒人的記憶就夠了,積極的作用已經有了,并不比“硬件”的影響更不為久遠。
保留記憶,不要忘記歷史,任何時候都要勇于面對歷史,民族才能不斷強大起來,同時付出更少的代價。
19年結緣“1942”,馮小剛昨日答本報記者問:
我終于把不可能的事變成一種可能
談起電影拍攝的初衷,馮小剛說:“我和這個題材有一個緣分。”這個緣分要回溯到將近20年前。
1993年,王朔把劉震云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拿給馮小剛看,馮小剛一口氣讀完,感覺“很有意思”,但這個小說沒有故事、沒有人物,也沒有情節。
談起讀后感,馮小剛說:“對我的觸動非常大,覺得非常吃驚,完全不可想象中國人的生活是那樣的。”并且,現實是“餓死這么多人的事似乎很少被人提及”。這使他開始重新想“我們的民族性問題”:我們是從哪兒來的?
隨后,馮小剛幾次給劉震云提出要把小說拍成電影,“震云都不接這個茬”。2002年春節的一個晚上,兩個人在馮小剛家喝過酒,劉震云說:“我今天來有件大事,我想把《溫故一九四二》這苦孩子正式托付給兄長了。”
于是開論證會,結果不出所料,所有專家不約而同否定了拍電影的想法,理由很簡單:沒有故事、人物和情節。
馮小剛卻認為,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事,那才有價值,劉震云對此也深表認同。
然而,因各種原因,電影拍攝還是幾度擱淺。
2010年,電影《1942》拍攝以2.1億元的投資再度啟動。馮小剛率領他的團隊,橫跨7地、拍攝了135天,“艱苦卓絕,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努力,吃了難以想象的苦”。在拍攝過程中,馮小剛“重新審視了民族性問題,我們在災難中會淪落出一種奴性”。
2012年11月29日,《1942》將在各大院線公映,歷經19年艱辛,馮小剛“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很高興,這么多年,終于把電影拍成了,能把理想實現了。”馮小剛喜不自禁。
與其他災難片不同,電影結束后,觀眾沒有掌聲,這意味著什么?馮小剛說:“之前我們做了很多試映也是這種情況,觀眾看了電影,很長時間走不出去,這說明對觀眾觸動很大。”馮小剛說:“觀眾需要不同的電影,有快樂的、有宣泄的,《1942》有自己的觀影感受,觀眾覺得有收獲,沒浪費錢,就是值得的。”
對《1942》,馮小剛說:“希望觀眾看到一個好的、打動人的故事,同時也能引起一些思考。”他尤其希望年輕人能靜下心來,到影院看看這部電影,“還是很有價值的”。
在張國立看來,這種“價值”就是“人的尊嚴是從肚皮開始的”。
對劉震云,馮小剛還是一如既往地推崇:“好電影是由好作者決定的,《溫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說,震云又創造了非常好的劇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文/本報記者 閆伊默 圖/本報記者 史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