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06 09:22:00 來源:映象網綜合
網友評論0條 查看全文(共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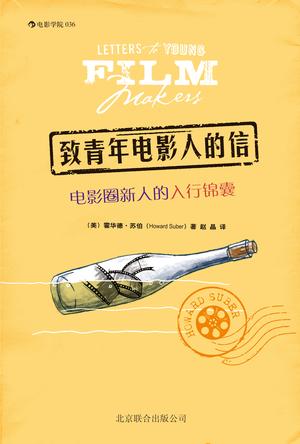
致青年電影人的信:電影圈新人的入行錦囊
內容推薦
本書是UCLA電影學院教授霍華德·蘇伯為初入行的青年電影人答疑解惑的一本書信集,精選自5000多封向他求助的往來電子郵件,涉及了導演、制片、編劇等各領域。作為電影教學領域的帶頭人和電影制作行業的資深顧問,霍華德對電影工業有著十分深刻的理解,他在信中直率而友善地解答了關于創造力、人脈、靈感、觀眾需求、談判能力、版權等各方面的問題,強調在個人職業生涯中,電影人不僅要具備專業技能,更要懂得處理創作過程中必然面臨的現實問題,培養這方面的應對能力。
對剛剛畢業的學生和等待拍片機會的新手而言,書中風趣而冷靜的建議是一貼“苦口良藥”,幫助你了解業內規則,拋開偏見,正視現實和理想的差距,從新手成長為一名專業電影人。
作者簡介
霍華德·蘇伯執教于著名的洛杉磯加大電影學院,好幾代編劇、導演、制片人、動畫師和電影學者都師從于他;他的學生如今在世界各地從事電影、電視創作,或教授電影研究課程。
在洛杉磯加大從教四十六年的時間里,他教授的影視課程多達65種,其中包括:編劇、導演、制片、電影史、電影理論和電影批評等等。他創立并主持了洛杉磯加大當前的影視制片人項目,該項目以關注現代影視行業的現實為焦點。他曾聘請業內許多最重要的制片廠主管、經紀人、制片人、律師和行政高管為學生們授課,并與其中一些人聯合授課。
在蘇伯前一本書《電影的力量》前言中,圣丹斯電影節前任主席杰弗里?吉爾摩曾寫道:“霍華德·蘇伯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老師之一”,“他精力充沛、博采眾長,極富創新活力”。他的這些特點和成就經由洛杉磯加大師生認可,授予他洛杉磯加大最杰出教師獎,他還因此在電影節上兩次獲頒終身成就獎。
在象牙塔外,霍華德·蘇伯的名字也是如雷貫耳,受人尊重。影視公司聘請他為顧問,為公司的商業戰略計劃獻計獻策,并為公司人員講解電影商業的本質和結構。在過去四十多年里,他作為顧問和專家見證人曾參與過著作權、創意控制、創意流程和版權等等問題的處理。《電影的力量》被廣泛用作編劇和導演課程教材,已被譯為中、日文。蘇伯至今仍前往世界各地教授有關美國電影和美國電影業的課程。
趙晶,先后獲得外交學院英語系學士學位和中國電影藝術中心電影學系碩士學位。現任職于中國電影資料館,主要從事國際電影文化交流和推廣工作,另譯有《簡明世界電影史》。
精彩試讀
05 最重要的創造力原理
霍華德:
你曾經提到你以前開過一個關于創造力的研習班。我對于創作過程很有興趣,我在亞馬遜網站上搜索相關書籍時,發現有上百本書,卻不知從何入手。你認為哪本書最主要?最核心的創作觀念是什么呢?
親愛的邁克爾:
的確有很多書試圖講述更富創造力的方法,這好比要告訴別人怎么才能更有趣一樣。但也有一些書是描述前人創作方式的,還有一些是努力尋找創造力的基礎的,比如阿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的《創作行為》(The Act of Creation)。五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觸這本巨著。雖然有人批評它對創作問題的處理過于簡單,尤其是那些持不同理論的人,但它卻可能是我引用最頻繁的一本書。
阿瑟·克斯特勒杜撰了“異態混搭”(bisociation)這個詞,并頗具說服力地指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創造力、科學發現和幽默感都來源于此。它意味著將此前從未并置或經常被認為不該并置的元素搭配在一起,從而創造出全新的、有用的或幽默的事物。
異態混搭并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辯證法,被并置的事物也并不具備必然的矛盾關系, 只是從未有人將二者組合過而已。
在影片《異形》(Alien,1979)中,當全體宇航員再次圍聚在一起吃飯聊天時,氣氛本來十分融洽, 突然異形怪胎怪叫著從其中一人的胸腔中掙脫而出,為影片的片名角色創造了戲劇性的出場方式。在《終結者》片頭,前一秒表現加利福尼亞南部天空出現的一道道閃電強光,下一秒人行道上就“降生”了一位全裸美戰神。在《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中,畫面中標有知名航空公司名稱的宇宙飛船停靠進旋轉的巨大太空站,背景音樂響起的卻是約翰?施特勞斯于19世紀創作的《藍色多瑙河》。音樂捕捉到畫面的優美與典雅,但由于二者時代不同,這種并置貌似不妥。
異態混搭通常是將意想不到、令人生厭,有時甚至是“反常怪異”的事物并置在一起,這也就是為什么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科幻片和恐怖片總會使用這種技巧,將兩種文化(地球文化和異星文化)或兩種存在狀態(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組合在一起。
喜劇更少不了異態混搭。那些少有共同之處、看似“不配”的男女總是會走向愛情,比如《熱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安妮?霍爾》、《畢業生》(The Graduate,1967)、《窈窕淑男》(Tootsie,1982)、《孩子們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2010)等等。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要學會恰當地將此前被分置的兩個或多個不恰當的元素組合在一起。我并不是說只有異態混搭才是創造、實現幽默或取得重要發現的唯一渠道,但是我要強調這個概念非常有用,而且經常被廣泛應用。
我經常推薦的另一本書是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ály Csikszentmihályi)創作的《創造力:發明與創新的流動與心理學》(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作者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主任,這本書和它的姐妹篇《流動:最佳體驗的心理學》(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是作者長期研究那些被同行視為行業領軍人物的藝術家、科學家、發明家和其他創造型人才的結果。
克斯特勒在檢驗創造性產品的生成過程,而奇克森特米哈伊考察的是創作者的關鍵心理。他發現創作人員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時,狀態最活躍,也最容易心滿意足,無論具體的工作內容是演奏樂器、繪畫、制陶,還是執導、編寫或監制一部影片。在這種時候,創作人員報告說他們會忘記時間,很專注(外人會說他們沉浸其中),通常會產生一種心理學家所說的“海洋感”——天人合一,不受阻力,隨之流動。那些調查研究冥想和禱告的人也談到過這種完全沉浸其中時產生的海洋感。
一些人在構建自己的生活時,為之填滿了會議、疲于應付的工作和現代生活中的各種消遣娛樂項目。如此繁多的任務只會令創造力銳減或幾乎降為零。奇克森特米哈伊在他的書中說道,對于創作感消失的恐懼普見于各種創作人員身上。當恐慌趁虛而入,你便深信“我再也沒有好點子了,我永遠都無法編寫、執導或監制出另一部新片了”。
創作人員的生活應當這樣安排:讓自己能夠沉浸在工作之中,盡可能地去感受“流動”感,然后將此前從未并置的事物混搭起來。這些書不是教你該怎么去做,但是的確告訴了你別人是如何做到的。
11 如果劇本真那么重要,為什么編劇經常被貶得一文不值?
霍華德:
我說這話可能聽起來像是喜劇演員羅德尼·丹杰菲爾德(Rodney Dangerfield)在舞臺上抱怨自己不受尊重一樣,可我的確不受尊重。我是一名編劇,我的很多朋友也都從事編劇工作。我們總是發現我們成為了犧牲品。雖然許多制片人都喜歡說,我們寫的劇本是影片的核心,沒有“藍圖”,他們就得不到制作經費。可是為什么他們總是輕易解雇我們,或者在游戲剛一開始就把我們踢出局呢?有時我們完成一個劇本要花好幾年的時間,可一旦賣出后,就只能跟它“沙揚娜拉”了。更別提我們少得可憐的薪金了,連明星或導演薪酬的零頭都不夠呢。為什么但凡是個人就覺得自己能比編劇寫得好呢?
親愛的克拉麗斯:
在洛杉磯加大的制片人項目中,每年會有三四百名頂尖的影業主管、制片人、導演和參與電影制作的其他人員出現在課堂上,與學生們分享他們的從業經驗。實際上,他們每一個人的開場白都無外乎:“一切都始于一個好劇本”,或“如果不寫在紙上,也就不會搬上舞臺”,或“一個壞劇本,拍不出一部好影片”。
彼得·古貝爾(Peter Guber)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制片人,在我與他聯合執教的八年期間,他正擔任索尼影業的首席執行官。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樣決定是時候改變一下了。于是,我當晚去旁聽了他的課。他請來了大制片廠的三位高管,每個人的開場白都與我此前引述的沒什么差別。在提問環節,我舉起手問道:“如果劇本真那么重要,為什么編劇卻經常被貶得一文不值?”
課堂上發出了陣陣笑聲,但講臺上的人卻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然后,三位大制片廠高管依次對劇本的重要性進行辯護,每個人都表示對編劇有著崇高的敬意,有些編劇還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但是,對于我提出的編劇的境遇問題,他們并沒有發表任何爭論。
難道這些電影業的當權人士在說沒有好劇本就一無所有時是在說謊嗎?我認為不是。他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們信以為真,他們之所以信以為真是因為他們是聰明人,他們之所以是聰明人是因為他們知道事實的確如此。既然如此,編劇的境遇為何還是這么糟糕呢?我認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1)人人都認為自己是編劇;(2)編劇最早撤離工作現場;(3)有時,這是編劇咎由自取。
編劇是少數的電影主要創作人員之一,他們出售的是有形的產品。他們創作的產品被律師稱為“可轉讓”物品,即可與創作者分開、被單獨處理的物品,也正因如此電影業經常把劇本視作一項“資產”。
一旦擁有這項資產,你就不再需要它的創作者了。即便創作完全由編劇自主完成,劇本一經出售給制片人或大制片廠,編劇便自動放棄了作品的所有權利(這幾乎是不容侵犯的原則)。作品出售后,如果他們還讓你繼續參與修改,就算你幸運了。這樣的話,你需要簽署一份合同,按照合同規定你只是“雇傭編劇”,因此,這也就意味著你可以隨時被解雇。
而導演和演員并不出售產品,他們出賣的是與本人不可分割的服務。雖然導演或明星也可以被解雇,但這種情況極少發生,其主要原因也有三個方面:(1)這通常意味著要推翻已經拍攝完成的部分,一切從頭再來;(2)導演和明星都不愿意接替同行的活兒(但編劇卻絲毫沒有這方面的顧慮);(3)這將危害到影片的聲譽,此后將永遠貼上“問題”影片的標簽。
沒有一位首席執行官、制片部主任、制作副總裁、研發主管、制片人或其他掌權人士膽敢跑去片場指揮導演該怎么拍電影。他們也不敢建議攝影師該使用哪只鏡頭,或告訴作曲家該用哪個主調進行創作。
但首席執行官、制片部主任、制作副總裁、研發主管、制片人,以及初級研發管理人員、劇本審讀員、制片助理,甚至勤雜工都無一例外地、可以毫無顧忌地在編劇該怎么寫劇本方面指手畫腳。為什么他們覺得自己有權這么做呢?
首先,從事當代電影制作的絕大多數人都上過大學,其中還有一大部分是研究生,在學校里他們讀了大量的故事,也進行過不少文字創作。他們可能沒寫過劇本,但是他們對寫作并不陌生。他們對于攝影機構圖、運動或照明燈的細微之處可能所知甚少,所以他們不太可能去指揮導演該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們對于片孔、鏡頭光圈或焦平面也可能一無所知,所以他們也不會去找攝影師的麻煩。雖然他們有可能和導演一起走進剪輯室并提出修改建議,但他們也只是把建議提給導演,絕不會指揮剪輯師進行具體操作。然而,那些掌權的人卻總會認為自己有資格評判情節、人物和對話的好壞。
故事的另外一面你可能不會喜歡,而我的職責是盡可能客觀地描述世界,如果我不告訴你這許多年來我在私底下從制片人或導演那里聽到的話,我會覺得自己很失職。
這些人說,編劇通常是個大麻煩,他們表現得就跟自己是影片的作者似的,但實際上他們并不是,他們只是創作了劇本而已。
我非常尊重文筆好的人,但電影卻并不僅僅是寫作這么簡單。小說只是基于某個人用筆書寫,戲劇是基于別人寫作的一種表演,但是,電影則是將表演、導演、攝影、剪輯、聲音、音樂、燈光、布景設計、外景地等等因素組合在一起的綜合創作。上述各項的重要性不分先后,因為在某部影片中最關鍵的元素在另一部影片中可能只發揮了次要作用。
如果讓編劇跟你說說他們和制片人或主管交手的情況,他們總是會給你講上很多故事,還會盡情講述他們收到的那些愚蠢的建議。僅有一兩次,我聽編劇說過制片人或主管提出的建議還不錯。聽了幾十年類似的故事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笨蛋在掌管影業大權。我遇到的很多行政主管和制片人都非常聰明,受到過良好的教育。越有經驗的制片人或主管提出的建議,編劇就越應該認真地聆聽。
通常情況下,制片人和主管抱怨編劇根本聽不進去他們的建議。有時,編劇總是沉浸在自己對劇本的構思之中,他們無法打破這個框架,也無法在已完成的作品中再進行大幅度的刪改。而有時候,只是他們不愿意這么做而已。
事實上,理解劇情、人物和對話并不是只有編劇才會干的事兒。當編劇表現得仿佛只有他們才有能力進行判斷,而那些掌權的人又覺得自己知道的一點也不比編劇少時,也就難怪編劇會被貶得一文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