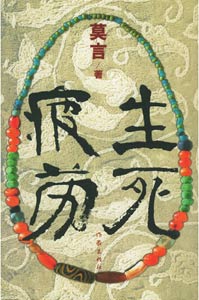
《生死疲勞》
內容簡介
小說敘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50年的歷史,圍繞土地這個沉重的話題,闡釋農民與土地的種種關系。小說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闡釋著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而另一個主人公即小說的敘述者,則在六道輪回中,一世為人、一世為馬、一世為牛……從不同的視角講述他所看到的故事。小說透過生死輪回的藝術圖像,展示了建國以來中國農民飽經患難的生活和他們頑強、樂觀、堅韌的生命。故事情節極端、怪異、變形、荒誕,但是與寄寓其中的哲理渾然天成。全書從內涵到外延充滿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滿了藝術靈氣。究其所達到的藝術境界而言,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史詩性作品,是中國文學終于跳出圖解概念沼澤最輝煌的標志性著作。
媒體評價
莫言解讀: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
■書名來自佛經。《生死疲勞》來自佛經中的一句:“生死疲勞由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莫言說,佛教認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擺脫令人痛苦的六道輪回,而人因有貪欲則很難與命運抗爭。
●寫作速度創紀錄。莫言只用43天寫就長達55萬字的《生死疲勞》。從八月起,最多一天寫作1.65萬字,平均一天只睡三小時,突破了他自己寫作速度的最高紀錄,自稱睡覺時也有一半的腦細胞在工作,有的夢也變成現實。
■以人物的命運作突破口。“沒有土地,農民像浮萍一樣飄搖。”莫言稱,20世紀80年代之后,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的經營者。如今,“當年眷戀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土地。”莫言說,農民飽經患難的歷史,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螺旋上升的歷史規律。但他坦言,寫作的時候,他并未按照這一規律寫作,而是以人物的命運作為突破口。
●探索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莫言認為,歷史大致由兩種人物擔當,一種人是有價值的個性,而另一種人是無價值的個性。《生死疲勞》中就有這樣的兩個主人公。“這是個性相似的兩個人走了不同的方向,互為正負,合起來是一個人,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莫言VS李敬澤:現在的農民不愛土地?
■李敬澤:土地原是農民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但現在它正在農民的心中瓦解。新作堅持以土地為中心,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
●莫言:農民和土地是親密的關系,一旦逃離土地,農民就沒有了根本,會陷入更深的苦痛。幾千年以來中國改朝換代、農民起義,圍繞的核心問題都是土地。1949年之后,農村的變遷實際上還是土地的問題。《金光大道》和《艷陽天》說的都是土地的問題。寫農村改革的小說實際上并未涉及根本,根本問題就是“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到了今天,這種關系又發生了變化,農民紛紛逃離土地,出現新一輪的土地荒蕪現象。
■李敬澤:但現在的問題是,這個中心在當下生活中、在農民心中正在瓦解。而在小說中,你堅持了這個中心,這是對現實的一種回應?
●莫言:莫言:我還是認為,農民和土地還是親密的關系,一旦逃離土地,農民就沒有了根本,我認為,不應毀掉或背棄土地,那必將使農民陷入更深的苦痛,前途更加未卜。我無法預見,也無法解決,但在我小說的結尾,展示了逃離土地或背離土地的凄慘景象。當然最后還是有希望的,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
■李敬澤:在佛教中,六道輪回是為了破“執”,也可以說,《生死疲勞》是一部關于“執著”的頌歌和悲歌,人之所以苦就是因為放不下,最終安放我們的是這片土地。
■莫言:一切來自土地的,最終也回到了土地。可是,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愛土地了。
■李敬澤:《生死疲勞》是一部向我們偉大的古典小說傳統致敬的作品。這不僅指它的形式、它對中國經驗和中國精神的忠誠,也是指它想像世界的根本方式。現代小說已經遺忘了這樣的志向,而《生死疲勞》讓我們記起了那種宏大莊嚴的景象。
■莫言:只要跟《檀香刑》不一樣就行,別的咱也不管。
莫言新作觀《生死疲勞》
莫言的新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出版,它以“輪回”的構架闡釋了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是作家出版社在圖書訂貨會上投放的一枚重磅炸彈。
有評論家認為,在大多數人認為“鄉土文學已死”之時,《生死疲勞》擲地有聲。
鄉村歷史中的人物個性有無價值?
《生死疲勞》是由一個人在不同輪回中看到的片段構成鄉村歷史。“土地問題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把鑰匙。”莫言表示,新作敘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50年的歷史,圍繞土地這個沉重的話題,闡釋了農民與土地的種種關系。
莫言認為,歷史大致由兩種人物擔當,一種人是有價值的個性,而另一種人是無價值的個性。《生死疲勞》中就有這樣的兩個主人公。
“我相信這種農民在全中國也為數不多”。莫言向記者分析了小說中的主人公,一位一直未加入合作社農民。書中,“文革”的浪潮使他比地主還悲慘,他遭遇到來自各方的打擊,眾叛親離,但他還是執拗地堅持單干。到了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當年的農民回頭看他,發現歷史轉了一個圈,他竟然是有前瞻性的。
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一個村支書,他是個正派的基層干部,到了20世紀80年代,他看不慣一切,希望恢復人民公社,為此他不惜以死相拼,死時還高唱《國際歌》。
莫言感嘆,當時違背思潮的農民恰恰被歷史證明是“有價值的個性”,而以死相拼的村支書恰恰被歷史證明是“無價值的個性”。
“這是個性相似的兩個人走了不同的方向,互為正負,合起來是一個人,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六道輪回中以動物之眼看世界
莫言說,書名《生死疲勞》來自佛經中的一句:“生死疲勞由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他說,佛教認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擺脫令人痛苦的六道輪回,而人因有貪欲則很難與命運抗爭。他是在承德參觀廟宇時,偶然看到有關“六道輪回”這四個字而激發了創作靈感。
據他介紹,小說的敘述者,是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他認為自己雖有財富,并無罪惡,因此在陰間里他為自己喊冤。在小說中他不斷地經歷著六道輪回,一世為人、一世為馬、一世為牛、一世為驢……每次轉世為不同的動物,都未離開他的家族,離開這塊土地。小說正是通過他的眼睛,準確說,是各種動物的眼睛來觀察和體味農村的變革。
新形態的鄉土文學方興未艾?
“沒有土地,農民像浮萍一樣飄搖。”莫言稱,20世紀80年代之后,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的經營者。
如今,“當年眷戀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土地。”莫言說,農民飽經患難的歷史,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螺旋上升的歷史規律。但他坦言,寫作的時候,他并未按照這一規律寫作,而是以人物的命運作為突破口。
2005年賈平凹的新作《秦腔》遭到評論家的批評,對于“從這部長篇小說的失敗可以為中國鄉土文學畫上句號”
這個說法,莫言認為“這個結論有點絕對”。他表示,以《創業史》、《金光大道》為代表的鄉土文學是終結了,但是新形態的鄉土文學方興未艾。
他分析,農民已經不再是商品的生產者,已經融入國際大市場,所以鄉土文學也在自覺地縮短和城市文學的距離,這是新形態的鄉土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