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1 09:45:00 來源:騰訊娛樂
網友評論0條 查看全文(共1頁)
第6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正在舉辦當中,寧浩的《無人區》、婁燁的《推拿》和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三部內地電影入圍主競賽單元引起轟動;尤其是《白日焰火》,以一種橫空出世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不少非業內人士都很好奇:這個片子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其實,該片導演刁亦男在業內赫赫有名:《愛情麻辣燙》、《洗澡》、《將愛情進行到底》等影視作品的劇本都出自他筆下;《制服》、《夜車》等導演作品也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入圍過戛納“一種關注”、釜山“新浪潮”、鹿特丹以及溫哥華電影節,可對于國內普通觀眾來講,是今年的柏林電影節才讓他“浮出水面”。
與刁亦男類似,當年的張藝謀、王小帥、顧長衛、王全安等人,也都是通過柏林電影節才“一舉成名天下知”。既然柏林電影節這么牛,那么到底該怎么拍片才能被它相中?騰訊娛樂通過搜集整理歷史數據,分析其中規律并請來業內高手點評,總結出一套“柏林電影節攻克指南”,希望能為那些有志于電影的年輕導演提供一點借鑒。
政治和民族題材具有天然優勢

《紅高粱》劇照
柏林電影節創辦于1951年,當時德國正出于分裂之中(東德和西德),因此從創辦之日起,它就對戰爭、政治和民族題材電影保持著天然的敏感,這種敏感直到今天仍然還在。
就華語電影來講,最早在國際上獲得大獎的是張藝謀的《紅高粱》,該片改編自莫言的同名中篇小說,站在孩童的視角、以極其特殊的方式描繪了中日戰爭,于是在1988年獲得了第三十八屆柏林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這是中國第一部獲得“金熊獎”的華語電影,也是第一部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獲得最高獎項的華語片。

《圖雅的婚事》劇照
如果說《紅高粱》已經過于久遠、且由于是戰爭題材,一般年輕導演導演駕馭不了的話,那么近年《圖雅的婚事》則更具借鑒意義。這部由王全安執導、余男主演的影片,講述了一個內蒙女子“嫁夫養夫”的故事,不但充滿了異域風情,還展現了困境中人性的掙扎。該片在2007年獲得柏林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王全安在談及為什么要把故事背景設置在內蒙時曾表示:“如果把這個故事放在漢族的家庭里,一定是個挺郁悶的電影,充滿了掙扎、沉痛,少數民族地區不會那么多禁忌,我可以借蒙古族的膽讓我奔放一下。” 而今年入圍主競賽單元的《無人區》,則拍攝于新疆,具有濃郁的西部風格。
人物傳記片更容易“名利雙收”

柏林電影節華語片入圍指南
不論奧斯卡還是歐洲三大電影節,“名”和“利”往往是分開的:在市場上大賣的商業片往往不會獲得電影節青睞;相反,在電影節上獲得大獎的影片雖然有名,但往往又因為藝術性過強不會獲得太多普通觀眾認可。
但有一點例外,那就是人物傳記性質的影片容易名利雙收,這一點在柏林電影節上體現得尤其明顯。關錦鵬執導的《阮玲玉》當年在香港轟動一時,也讓柏林電影節為之傾心,阮玲玉的扮演者張曼玉于是在1992年的第四十二屆柏林電影節上榮膺影后,這是柏林電影節的首位華人影后,也是第一個歐洲三大電影節的華人最佳演員。
除了《阮玲玉》,《大太監李蓮英》和《梅蘭芳》也都曾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其中陳凱歌執導的《梅蘭芳》雖然沒有最終獲獎,卻在內地獲得了大約1.8億人民幣的市場回報,這在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中并不多見——張藝謀當年的《三槍拍案驚奇》和今年的《無人區》都算是極少數例外。
展現“老少邊窮”很受歡迎

《盲井》劇照
展現中國的“老少邊窮”或陰暗面曾經很容易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受到歡迎,柏林也不例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李楊執導的《盲井》,它展現了中國某個特定區域的貧窮落后以及人性的極端貪婪,于2003年獲得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節“特別藝術貢獻獎”。
張藝謀的《紅高粱》、《我的父親母親》以及王全安《圖雅的婚事》、《白鹿原》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現了中國不同時期落后的一面。
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展現中國的“老少邊窮”或陰暗面并非華語電影人的目的所在,他們只是想通過電影回顧歷史或探討人性,但客觀結果卻是讓中國看起來很不光彩。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就曾當眾對媒體抱怨:“我就不明白了,印度的電影人把自己的國家拍得那么美好,但實際上并不是那個樣子。為什么我們的電影人非要把自己的祖國母親拍得那么丑、難道丑我們就光彩了嗎?”
也正因為如此,對于中國的年輕導演來說,雖然展現中國的“老少邊窮”或陰暗面比較容易獲得國際關注,但也要承擔一定的現實風險,比如作品不能在內地公映或必須大幅刪減等,具體該怎么取舍恐怕只能留給當事人去作決定。
大尺度情欲題材屢戰屢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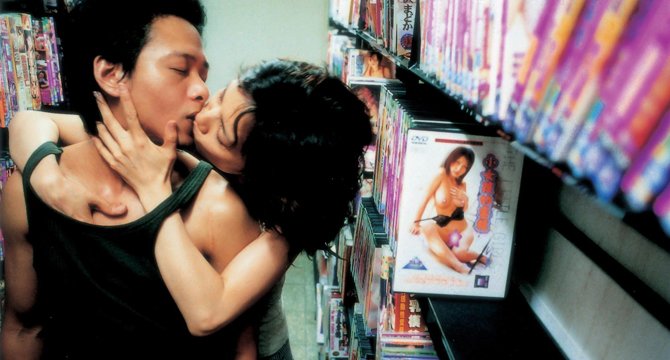
通過情欲展現人性是世界電影的一大主流題材,柏林自然也不例外。
2007年,由李玉題執導,佟大為和范冰冰主演的《蘋果》曾與《圖雅的婚事》一起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雖然沒有最終沒有獲獎,但造成的話題和影響比獲獎還大,甚至一度導致該片在內地被禁映。
蔡明亮執導的情色電影《天邊一朵云》,曾于2005年在第五十五屆柏林電影節上獲得特別藝術貢獻獎、阿爾弗雷德·鮑爾特別創新獎和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三項大獎,風光無限。
可由于中國內地沒有電影分級制,大尺度情欲題材電影雖然容易出彩,但如果想要在內地公映且不肯刪減的話,可能性不大。
有海外投資入圍獲獎水到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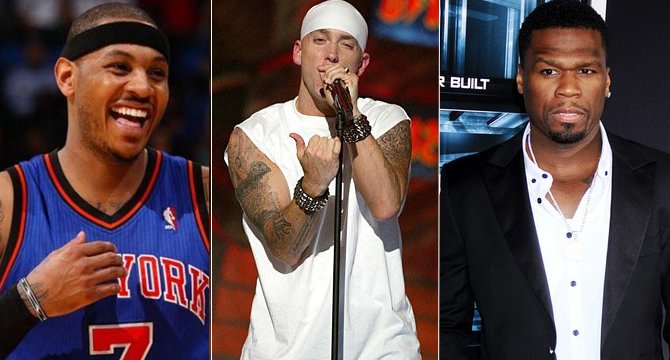
柏林電影節華語片入圍指南
部分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有些華語片在“成名”之前悄無聲息,然后忽然有一天它們就成了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座上賓。
一位資深業界人士向記者透露,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影片中不少都含有海外投資:“歐美地區有不少支持獨立電影的基金,它們和中國的不少導演都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一旦你的影片含有海外投資,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甚至獲獎當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大陸比較有名的導演中,賈樟柯、張元、王小帥、婁燁等人在海外融資方面都很有門道,他們的電影屢屢成為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也就不難理解——畢竟人家老外花錢拍的片子,難道不能入圍一下自己舉辦的電影節么?
比如王小帥的成名作《十七歲的單車》曾獲得第五十一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其投資就主要來自海外。張元的《看上去很美》曾在柏林電影節獲得“杰出電影藝術創新獎”,其海外投資則自來自意大利國家電視臺和意大利國家電影制片廠。幾年前婁燁執導的《花》曾被選為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的開幕影片,不過其身份則干脆是法國片。今年入圍主競賽單元的《白日焰火》,據傳其海外投資人甚至包括NBA巨星卡梅隆·安東尼、嘻哈歌手艾米納姆、50分等,絕對是“后面有人”。
柏林電影節提倡個性 更傾向年輕導演

柏林電影節華語片入圍指南
體現自己的政治傾向、展現中國的老少邊窮,一度是內地電影人叩開柏林大門的敲門磚,可時代在變遷,如今的柏林電影節不僅傾向“老少邊窮”和弱勢群體,更提倡個性至上。2005年,顧長衛執導的《孔雀》曾獲得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可它不屬于上面任何一類電影;2010年入圍主競賽單元的《三槍拍案驚奇》也是因為個性獨特才被柏林選中。今年,“個性至上”體現得更加明顯:三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影片,《無人區》是西部風格的犯罪題材,《白日焰火》帶有愛情、懸疑和犯罪等諸多元素,《推拿》展現的則是盲人按摩師的心理和人生,沒有任何一部與政治沾邊,也沒有展現中國的老少邊窮。
談及這一點,柏林電影節主席迪特·科斯里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年輕導演的創作力非常旺盛,與上一輩導演擅長歷史性題材所不同,新導演們喜歡的題材范圍更加廣泛,并且創作方式更加多元化,而這也正是柏林電影節的發展方向。
前上海國際電影節業務副總監、《白日焰火》監制、對世界各大電影節選片規則了如指掌的沈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說,不同的電影節有不同的定位,柏林更直面工業本身:“今年的競賽片選擇,更體現出電影節在導演或者是創作生態遭遇不順時給出強有力的幫助,在他們的上升階段關注并支持他們,這倒更像之前戛納電影節主席Gilles Jacob曾經表達過的一種態度,但現在柏林貫徹得更徹底,戛納和威尼斯反而因為老牌而更瞄準現存大師及其作品。”另外,沈暘還表示,參加電影節是一個綜合考量:它還跟你影片準備何時投放國內市場、傾向于找哪種類型的國際發行等等各方因素相關。不同的國際發行擁有不同的國際電影節資源與經驗,不同的電影節時間段又分別應對著不同的國內市場檔期。”
不過沈暘強調說,中國電影的話題景觀永遠高過制作本身,這是我們將來必須要調整的一個方面。她以《白日焰火》舉例說,該片從最早的項目入圍鹿特丹電影節、釜山電影節到后來的上海電影節等項目市場,一直到現在呈現在公眾視線下,經歷了近6年的時間:“導演對劇本的打磨用了三四年時間,以求達到他和制片人心中的標準。事實上,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劇本在業內廣為流傳,也正是這樣一個優秀的劇本,一下子就打動了桂綸鎂和廖凡加盟。這鐘創作態度正是目前浮躁的創作環境下值得年輕的入行者學習的。”